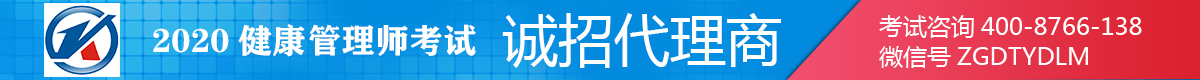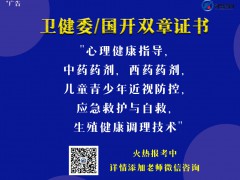《通知函》明确,临床研究实行医疗机构立项审核制度,临床研究须经医疗机构审核立项,医疗机构应与临床研究负责人签订临床研究项目任务书,并在3日内向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临床研究备案,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上传有关信息,已经开展(首例受试者已入组)但尚未完成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应当自本文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完成立项、登记并上传信息等工作。逾期未完成的医疗机构,不得继续开展临床研究工作。
对于临床研究的开展流程,《通知函》要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每日通过备案系统将辖区内医疗机构拟开展的临床研究相关信息汇总,转送至同级科技行政部门报送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组长单位科技部的办公厅,然后再由科研攻关组下设的药物研发专班(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专家研讨并提出是否推荐开展临床研究的书面意见,对推荐进入临床研究的品种,由科研攻关组办公室将推荐意见转至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会同医政医管局协调医疗机构承接临床研究任务。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跟进临床研究进展,汇总临床研究结果,转送同级科技行政部门,由科技行政部门报送至科技部。科研攻关组统一汇总相关研究信息,经组织专家审查,将效果较好的药品有关信息(包含建议用法用量、禁忌症和可能出现的毒副作用等)向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通报。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函》还提出,医疗救治组组织专家研究提出相关药品是否纳入诊疗方案进一步试用的意见,未纳入诊疗方案的“老药”,不宜涉及直接在临床大规模使用。
2月25日,国家卫健委、科技部、国家药监局曾发布《关于规范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治疗临床研究的通知》,统筹规范已上市药物的临床研究工作,并进一步明确开展研究的条件,该《通知》提出开展临床研究的药物应该为已上市药物,且经过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验证有效,研究机构应该是县级以上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其中包括方舱医院。研究责任人应该是副高以上的执业医师,能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预案和管理措施,医疗机构是临床研究的责任主体。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就掀起了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潮,据医谷小编通过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查询,截止4月9日02时01分,针对新冠肺炎开展的临床试验累计达到583项,涉及的药物包括连花清瘟、血必净、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磷酸氯喹、糖皮质激素、热毒宁注射液、宫血干细胞、参芪扶正注射液、八宝丹、金银花汤剂、金银花口服液、香雪抗病毒口服液等多个药物。

根据临床试验库的数据汇总,最早的一项新冠肺炎临床研究的的注册日期是1月23日,是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开展的“一项评价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感染住院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随机、开放、对照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注册日期则是4月9日,是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危重症患者心肌损伤及心脏功能:基于病历记录的观察性研究”。
在新冠肺炎临床试验由初期的几十项急速上升到几百项且还在不断增加时,很多业内人士表示出了担忧。
此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科研机构的多位卫生统计学与流行病学专家发表文章《关于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临床试验的建议》,对当下的新冠病毒肺炎的临床试验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上述专家指出,临床试验如果没有高质量的设计,“如样本量不足,对照组的选择不合理,分组的随机化与遮蔽执行不严格,疗效指标的评价标准不客观,加之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保障不充分,那么这些临床研究就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使得首试患者、研究者和管理部门的努力付诸东流。”
还有业内人士也指出,现在很多的临床试验都是小样本,不少也不是随机对照、双盲,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果,甚至有的还涉嫌挤占了资源,导致一些本来有希望的药物临床试验遭遇招不到病人的尴尬。
也由此,此次《通知函》提出,若有违反《通知》、《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的,以及有明显毒副作用或无明确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科研攻关组应及时要求医疗机构终止研究。

图片来源:医谷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资料整理
在上述583项登记注册的临床试验中,就有43项临床研究已经撤销,其中包括6分钟步行训练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运动功能影响的研究,坐式八段锦疗法辅助治疗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方案,以及还有脐血间充质干细胞、脐带血CIK和NK细胞、脐血NK细胞联合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等治疗新冠肺炎的多个临床研究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