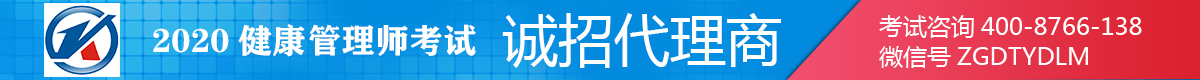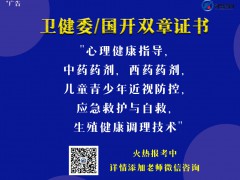7月22日,晚上九点半,张先生带着三位老人经过香港到深圳的关口,足足用了两个半小时。疫情前,在深圳工作的他每周都要通过的这个口岸和在香港工作、读书的妻儿团聚,只需要20分钟。
这两个半小时,需要填无数表格、刷多次二维码,繁琐的程序丝毫未让他感到漫长或烦躁,每一分钟都让他觉得离深圳更近一点,更安全一点。
1月24日除夕,在国内武汉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刻,带三位老人去香港过春节的他,已经滞留在香港近半年。几个月以来,张先生一直在等待香港和内地健康码互认,希望回内地不必隔离14天,但直至离开香港,他们也没有等到这一天,却等来了迄今为止香港爆发的第三波、也是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26岁的港漂女生梁书(化名),1月29号(大年初五)从上海飞回香港。7月之前,她最遗憾的事情是“半年没有去深圳了”。在她口中,深圳是“全香港的内地人都要去度假的后花园”,是她之前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的地方。
在深圳可以吃各种美食,玩狼人杀,去朋友家撸猫……一到深圳,她就觉得自己很“阔气”,阳光普照,马路宽阔,可以甩开膀子大步走,而在香港,要缩紧自己的双臂走路,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别人。
她起初和张先生一样,希望香港和大陆互通健康码。7月5日之前,香港两周无新增确诊病例,这一度让她认为,不久就可以解封去深圳。但香港的第三波疫情,不仅将她自由出入深圳的梦想打碎,每天的新增病例让她开始担心最坏的可能:如果自己一旦染上新冠,香港的医院人满为患住不进,而因核酸检测不过关,内地也回不去,自己只能“自生自灭”。
27岁的香港本地女生Zoe(化名),7月20日又搬回了她之前居住的明泉楼。这座30层,有近700户住户的香港公屋大楼,7月10日有11名确诊病例,占当天全港通报总病例的近三分之一。她一度避险搬出,但香港多个社区爆发确诊病例的现实让她意识到“哪里都有病毒,其实去哪里也有一样”,她宁愿回到确诊病例众多、但至少自己熟悉的住所。
这三位有不同背景的、短期或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人,同时经历了被疫情冲击三次的香港。
自7月5日开始的香港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短短二十几天,新冠确诊病例已达1600余例,超越前两波疫情确诊人数的总和。从7月22日开始,确诊病例连续7日破百。
截至7月28日,香港确诊人数已达2884人,远高于2003年的SARS。确诊人群已呈多点爆发,涵盖茶餐厅工作人员、养老院、政府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家庭主妇、菲佣、入境处、消防局、货轮、地铁工作人员、美心月饼员工等各行各业的人。
从2003年开始,香港在应对SARS、甲流、乙流方面已有成熟应对经验,也有着一群极其遵守规则、良好卫生习惯的市民。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一度,香港较为宽松的防疫政策,曾成功的遏制住两波疫情的传播,被外界视为抗疫典范。
但谁也没有想到,3个月之后,新冠疫情再次席卷香港。这一次,香港究竟怎么了?

△ 2020年7月27日,香港,两个人戴着口罩在维多利亚港旁聊天。来源:人民视觉。
极力保持平衡的香港防疫政策
7月22日,张先生离开香港住所的最后一刻,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在香港海滩上聚集的密密麻麻、不戴口罩的人群,叹了一口气。
实际上,有良好卫生习惯的香港市民群体,本身就有戴口罩的习惯。在疫情开始后,香港政府直到7月27日,并没有强制要求市民在室外戴口罩,虽然有不少市民主动在室外戴口罩,但在海滩和爬山这类场景中,却很少有人戴。
“在大陆,人们自觉的会比政策要求的多做一点;在香港,人们只执行政府的规定,不会多做规定之外的事情,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事情,人们就按照原来的情况做。”在上海长大,香港工作多年的梁书,更能理解两种文化的差别。
而香港的防疫思路,一直以来是根据疫情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以不破坏经济发展和最大限度保证人们日常生活为主要原则。在抗疫专家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看来,香港的防疫政策,是将本地疫情控制在“低水平”而非“清零”的程度。
因此,直到第三波疫情来临前,香港一直保持防疫政策的弹性调整,从未进行封城等最为严厉的政策,也一直未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过多的限制。
2020年1月下旬,梁书请了10天春节假期回家乡上海,因内地疫情发展,她担心香港会有临时的防疫措施禁止入境。她提前了几天回港,那一天,武汉封城已一周。上海的新冠确诊病例101例,香港的只有从武汉的输入性病例10例。在机场时,她没有感觉到香港和上海有什么不同:两边的机场和飞机上都很空,上海虹桥机场除了很多日韩的撤侨人士,本地的游客特别少。
到达香港机场后,入境检疫工作和往常没有区别,只是新增了一项——填写健康申请表。像往常一样、甚至比过去还要快,梁书等了二十分钟行李,就离开了。对此,她还在微信上和朋友吐槽:“根本没什么额外的措施,全靠个人自觉呀。”
一来到香港的大街上,她立马发现和上海的不同:上海的大街空空荡荡,而香港满大街都是人,5个月后的今天,她回忆起来:以大街上人群攒动的情况来看,香港的大街,2月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
上海与之相反,从过年之前疫情刚爆发,到春节时期疫情大爆发到慢慢稳定,梁书很多在上海的朋友,一个月都没有出过门。
从1月底到7月初,尽管在香港经历了两拨疫情,梁书的生活和往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香港,不会将全部的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关掉,政府制定的防疫规则,也是在有限的规则下,保证人们的日常生活。
梁书的公司让职员们轮流在家办公,疫情爆发时,梁书很少出门。到了6月份,在本地确诊病例极少的疫情低谷期,到了周末,梁书开始去逛街、在餐厅吃饭,或者去海滩、去爬山,和朋友们聚会。唯一和往常不同是,香港政府根据疫情的不同阶段,随时调整政策,实行了有限的“限聚令”,在室内聚餐一度不能超过4人,后来放宽至8人,随着香港3月中旬到4月中旬第二波疫情的过去,在6月份又放宽至50人。
在疫情期间餐厅也一直没有关闭,政府只是规定餐厅只能坐一半人,人与人坐的那一半之间,需要加一个隔板,防止飞沫传播。一些大型的商场如梁书总是去的海港城,这座集购物和餐饮与一身的大型购物中心,为了抵消游客减少的困境,不断给人们派发餐饮优惠券,那些周末,梁书都要去海港城吃“买一送一”的大幅度打折的美食。“餐厅前人们排着队,跟2019年没有区别。”
周末逛街完回家的梁书,经过中环,经过一个个天桥,还是像往常一样看到菲佣们,这是她们一周唯一和同乡聚会的日子。她们席地而坐,挨得很近,戴着口罩聊天,或者摘下口罩和同乡分享自己带来的食物。
这些场景让梁书觉得疫情很远,几乎不打扰她的日常生活。只是餐厅里的隔板,逐渐增多的聚集在户外聊天的人……让梁书觉得日子和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但这种不一样,像好莱坞大片中一个不起眼的标示,人们很容易绕过去,却因此绕不开巨大的风险。

不可控的输入性病例
形同虚设的居家隔离
3月31日,在初步控制3月初开始的香港第二波疫情时,香港大学医学院曾发表学术文章,称赞香港如何能在未完全封城的情况下阻挡住新冠疫情于本地大规模爆发:包括边境出入限制、隔离和建议确诊者、密切接触人群,让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但第三波疫情,恰恰是在控制边境输入上出了问题。
7月22日回到深圳的张先生,当天看到美国终于被香港列入高风险地区的消息,马上和香港的朋友们吐槽:“谢天谢地,美国终于被列入了。”
确诊人数超过400万人、几个月前就是全球新冠病例最多的美国,一直未被香港列入高风险地区,这种情况直到7月22日才发生变化,此时香港第三波疫情已爆发半个多月,新冠确诊人数已近2000人。
同时被香港列入高风险地区的国家有孟加拉、印度、印尼、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及哈萨克斯坦。来自这些地区的人,进入香港需持过往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香港的第一波疫情的输入性病例来自内地,这一波疫情,也是最快被控制的一次。香港政府早在1月25日就暂停往来武汉的航班及高铁;2月初那场医务人员罢工后,香港政府再次封闭多个口岸,并要求所有从内地抵达香港者,必须隔离14日。
对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内地及时采取封闭口岸等措施,是阻断疫情很重要的一步。但这一点,却未被复制到随后的两波疫情中。
到2月底,香港第一波疫情基本上被控制。但3月份,香港却始料未及地遭遇了第二波疫情,这次疫情主要是来自欧美的输入性病例。自3月22日至4月11日的三周时间内,每日输入病例不低于10人,累计输入病例达459人。
香港的很多家庭,都有子女在欧美留学,切断和欧美的联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欧美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香港3月23日提前预告,2天后将禁止海外地区人士入境。结果在随后的两天,所有的国际航班上都是逃回香港的人,对这些人,香港还不进行强制隔离或居家隔离措施,反倒促进了香港第二波疫情的传播。
让她觉得更不解的是,当同机有人确诊,除了前三排后三排,其他所有人都不会接到核酸检测或者隔离通知。
在梁书的印象中,香港第二波疫情的传播,在难以阻断海外输入性病例之外,对进入香港的病例传播,香港也没有采取集中隔离或核酸检测措施,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觉。
从海外回来的香港人,比较自觉。梁书有一个朋友在英国读书,在第二波疫情爆发前早就订好机票,她怕自己“千里送毒”,所以自己一个人默默订了酒店,在酒店里待了半个月。那个时候没有政府的主动隔离和检测,她在酒店里乖乖地每天给自己测体温。
但梁书的一些外籍同事就是另一种风格了,公司要求居家办公后,他们转而出去爬山或者喝咖啡。3月中下旬回来的一波外国人,开始到娱乐场所聚会,也成为传播很重要的原因。
一些可以入境的地区的居民(例如内地、澳门、台湾),香港要求他们居家隔离14天。香港政府也曾想过采取过集中隔离,但在征收宾馆上,遇到了麻烦,此计划就此搁浅,除部分群体如菲佣,政府要求集中隔离外,其余的大部分人群,主要还是依靠居家隔离。和大陆的管理人员具体到社区、整个家庭门上贴封条的居家隔离政策不一样的是,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的行政思路下的居家隔离政策,并非强制,而是依靠个人自觉。
张先生来到香港后,香港政府已经规定从内地来的人实行14天的居家隔离。他感到诧异的是,政府却没有规定他一直在香港工作的太太也隔离:她出去上班、购物是完全允许的。
香港政府发给隔离人士一个定位手环,薄薄的一层纸,和手机APP相连,手腕细的人轻轻一撸,就可以取下来。政府的检查政策之一就是给隔离者打电话,确认其是否在家中自我隔离?梁书的一个戴手环的朋友告诉她,完全有可能做到,把手机和手环都留在家中,然后出门。
6月中旬以后,疫情的平息,让香港政府和人民都放松了警惕。海外的一些机组人员等得到了出入境检疫豁免权,香港的娱乐场所也逐渐放开,限聚令也开放至50人。
疫情最新的调查进展证实,豁免检疫人士正是第三波疫情爆发的源头。7月28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香港电台节目中指出,根据专家基因排序实证,已收紧船员及机组人员的等人士检疫安排。
7月5日开始,第三波疫情的扩散,是海外输入病例的失控,遇到了在疫情低谷期放松警惕的人群,造成的结果。

△ 来源:香港卫生署。
最重要的核酸检测
可能存在采样失误的问题
7月19日,香港一天的新增确诊人数达到历史高点——100人,老人们的签证马上也要到期。张先生当机立断,准备回深圳。
按照深圳的要求,只承认从取样开始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结果。香港公立医院的免费核酸检测,根本排不上号,私人诊所985港币的优惠核酸检测套餐,因检测人数暴增,最快要2——3天才能拿到结果,不能保证期限。
7月20日,他们每人花1600港币做了加急特快的核酸检测,本该十小时之内拿到结果的“加急特快”,也因为检测人手不足以应对暴增的检测样本,推迟到了24小时之后。
张先生心急如焚,在不断的催促下,最终在72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
香港昂贵的核酸检测成本,是大陆的4—6倍,主要是香港从海外进口试纸,并未采用大陆价格低廉的试纸。
在第三波香港疫情之前,北京也曾爆发了小规模的新冠疫情。和香港不同的是,北京迅速锁定了传播扩散地,并通过对附近居民实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的方式,摸清感染规模,隔离感染人群。而香港昂贵的核酸检测成本和人手不足的核酸检测人员,阻挡了对人群大规模进行核酸检测的可能。
准备离开香港的张先生做核酸检测如此费劲,而因同座楼有确诊患者的香港女生Zoe,做核酸检测也并不顺利。

△ 水泉澳邨明泉楼居民深喉唾液检测通告。受访者供图。
27岁的香港女生Zoe住在沙田水泉澳邨明泉楼,这是一栋常见的香港公屋大楼,落成于2016年。同期建成的共有5栋大楼,楼高26至30层,共计3459个单元,也就是说,这5栋楼里密集居住着近3500住户。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公屋是政府或公营机构提供的低于市场价的房屋,在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这样的房屋中,这类楼宇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居住密度高。
7月7日,香港新增14宗确诊个案,其中9宗为本地个案,编号为1294号的66岁女性和Zoe住在同一栋楼,确诊前曾到访沙田新城市广场、沙田大围道13号和水泉澳广场。
Zoe有点慌张,她想知道确诊的人住在哪一层,但是并没有公开的信息。第二天,大楼贴出了一份通告,安排整栋楼的居民接受深喉唾液检测。所谓深喉唾液检测,即指采集深喉唾液样本。
核酸检测,与咽拭子采样是同样的原理。不同的是,咽拭子是由专业人员使用长棉签在咽喉部位取样,香港的深喉唾液样本的采集方式是,检测者自行提供深喉唾液。
当天,Zoe从大楼大堂领取了样本瓶和一份指南,她需要在起床后,刷牙漱口、饮食前采集自己的深喉唾液。具体的流程是,填写信息标签,洗净双手后打开样本瓶,以类似咳痰的方式清出来自咽喉的唾液,再将唾液吐入样本瓶,如果唾液量太少,还需要重复操作,完成后把瓶盖拧紧,将贴好个人信息标签的样本瓶装入样本袋,清洗双手后送回大堂。

△ 深喉唾液检测流程。受访者供图。
但Zoe对于自己采样是否准确,有点怀疑。一位医生认为,以吐唾液的方式自行采集深喉唾液,可能会存在采样失误的问题,一是可能操作不当,即能否采集到深喉位置的唾液;二是唾液本身可能会被污染。
7月9日到7月11日,这三天的早晨都可以交回样本。而就在7月10日,集中通报了11例沙田水泉澳邨明泉楼的确诊患者,在那天总共通报的38宗新增确诊中,其中32宗为本土个案,明泉楼占了1/3。
而这些信息,Zoe也只能从新闻中了解到,她还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层楼哪一户有人确诊。香港的做法是:递交样本后三个工作天内若无接获通知,即表示测试结果呈阴性反应,如测试结果呈阳性反应,有关市民会接获通知并获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
提交样本三天之后,Zoe一直没有得到任何音讯,她有些紧张,开始打电话到检测中心,得到的回复是“没有接到通知就应该没问题”。“对方甚至都没有问我叫什么,住在哪里,就这么回答我。”Zoe很生气。她估计,是因为检测中心的检测压力太大, 忙不过来了。
她自己就有一个朋友是在私人检测诊所工作,之前的日常工作是4小时在实验室,4小时在办公室做文案工作。“最近的情况是,他每天8小时都在实验室,根本没有时间做文案工作。”
离开的,留下的,同一天空下
7月中旬以后,香港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到了7月28日,已连续7天新增确诊人数过百。
香港政府在7月中旬,抗疫政策又做了几个有限的调整,例如因为7月初香港茶餐厅爆发疫情,政府规定餐厅早上和晚上不可堂食,只可取外卖。而考虑到香港公司的许多员工要上班,中午的堂食是放开的。梁书在中午经过餐厅,发现里面的一半空间都坐满了人,晚上依旧有聚集的人群在餐厅门口等待外卖。
直到7月27日,香港政府才要求市民减少外出次数,公共区域(无论室内室外)都强制戴口罩,禁止公众场合两人以上聚集,食肆全天禁堂食,关闭海滩等场所。
无论疫情和政策如何发展,生活还在继续。
留在香港的Zoe开始了居家办公。7月10日之后,明泉楼没有再通报新增病例,Zoe倒也不是很慌张,她觉得做好防护,应该不会感染。这几天,她都是在家做饭,乘电梯都使用餐巾纸或者笔来按楼层,进家门之前也会在门口喷洒一遍酒精进行消毒。
同样,梁书也开始居家办公,可以周末回深圳的梦想离她越来越远。随后的一段时间,她活动的范围将局限在自己的家中,通过窗口,能看到深圳的天空。
而已回到深圳的张先生,已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还记得离开香港那天,在香港遇到他最开心的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听说他们要去深圳湾口岸,那个司机笑着说:“1月底疫情刚开始时,最害怕去深圳口岸拉客人;现在一听客人要到深圳口岸,就开心,你们都有核酸阴性证明啊。”